北京地区佛教寺院文化特征初探
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时间:2022-03-22 14:50:28
北京的寺庙数量众多,在全国堪称首屈一指。清代乾隆时期绘制的京城全图中,共标出内外城寺庙1207所,以供奉观音为主的寺庵共占108处,为众庙之首;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的1631所中,佛教寺院占一半以上。虽然进入20世纪以来,寺庙数量直线下降,到1941年仅存783处(参见《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的寺庙》),但绝对数量在全国仍首屈一指。同时,梳理北京地区佛教寺院的历史渊源和轨迹,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历史机遇和文化氛围,衍化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约略言之,北京地区佛教寺院的文化特征,大体可归纳为“庙系天下”的政治色彩,“庙会商业”的世俗经济。“园林景观”的休闲场所,这三大特征互相包容,相互渗透,显示出“容纳百川”的文化内涵。这里,仅就北京地区佛教寺院的文化特征谈谈个人粗浅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时运机缘——北京地区佛教寺院文化特征的历史渊源与机遇
佛教最迟在西晋时已传入幽州地区。十六国时期此地区的佛教寺庙数量已经十分可观,虽经北魏太武帝“毁佛”,但总的趋势是处于发展时期。北周武帝“毁佛”时,幽州地区辖属于与北周对峙的北齐,不仅未受影响,更成为北周僧众“法难”的避难所。隋代时,更出现了沙门静琬凿经,炀帝的萧皇后施绢千匹以资刻经的盛事,幽州地区的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建寺也比较多。唐武宗“灭佛”时,幽州地区处于河北藩镇割据之中,对灭佛的诏令没有认真执行。关中、河东等地区的僧人纷纷拥入幽州地区避难。为了遏制这股潮流,唐廷封敕幽州节度使二把利刃,命其在居庸关斩杀东流的五台山僧人。五代时周世宗“毁佛”时,由于燕云十六州已割属契丹(辽),不在后周管辖之下,中原地区的僧人纷纷逃往幽州避难。
综上所述,中原王朝的三次“灭佛”运动,幽州地区不但没有被波及,反而成了僧众的避难所。北周至五代后周400多年的时间内,三次大规模地容纳外地僧人,带来无限的活力与新鲜血液,直接导致了幽州地区的佛教盛行,更奠定了北京地区佛教寺院包容万千、容纳百川的文化体系。
辽代的燕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契丹国志》),北宋时苏辙出使辽国,慨叹其已成为了“北国巨蠹”。辽代以后,北京地区基本上都是中原的政治中心,都畿所在,延续几百年的特殊政治地位,更为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元代的佛教无论是汉传,还是藏传,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寺庙建筑辉煌大度;明代寺院由于宦官的介入,更是出现了畸形发展;清代喇嘛庙迭起高潮,乾隆大规模修庙;直至近代,北京地区佛教寺庙才逐渐没落。
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发展轨迹和机缘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此地区佛教的寺院文化特征形成的历史渊源。
二、“庙系天下”——北京地区佛教寺院文化特征中的政治色彩
辽代以后,北京地区基本上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这基本上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从而演化出北京地区佛教寺庙关系天下兴衰的特殊文化特征与地位。这种政治色彩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面貌和角色出现,至近代以后逐渐淡出。
这种“庙系天下”的政治色彩在辽至清各个朝代共性的体现为数量众多的皇家寺院。辽代幽州地区许多寺院是在皇家直接支持下兴建、兴盛起来的,如云居寺、戒台寺、独乐寺、感化寺、悯忠寺等。金代中都地区在金熙宗、世宗时,寺院的修复和兴建出现了两次高潮,所建寺院规模更是宏大,如世宗大定年间新建的永安寺上下两院,不但耗资巨大,而且建成之后又大量赏赐田地、米粟和金钱。元朝皇帝下诏建造的寺院为数众多,如忽必烈建大圣寿万安寺,成宗建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和大承华普庆寺,仁宗建新华普庆寺,文宗建大承天护国寺。英宗在大都西郊寿安山唐代兜率寺的基础上修建寿安寺,“冶铜五十万斤”,铸造铜质卧佛一尊,更是豪举。而清代兴建的雍和宫、西黄寺、嵩祝寺、普胜寺也都是皇家寺院的典型。
明代“庙系天下”的政治色彩更与宦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代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宦官专政”(清代虽然前期秉承顺治遗诏“收宦官之权归之旗下”,以内务府掌管宫廷诸事,但慈禧太后秉政之后,太监又开始走红,出现了一大批宠阉)。作为“刑余之人”,“六根不全,无以为后”,向佛门布施修庙大种福田,不仅可以求得来世荣华富贵,儿孙满堂,光宗耀祖,更为自己修建了颐养天年之所。明代自永乐迁都后,在北京共建佛寺一千余所,其中大多是宦宫所建。有些著名寺庙名义上是朝廷敕建,实际上也是太监所修,区别只在于向皇上讨个名号而已。正如明人王廷相《西山行》诗中说:“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现有案可查、有史可考的一百多所明代寺庙中,有71所是宦官兴建。
清代“庙系天下”的政治色彩主要体现在喇嘛庙“怀柔抚远”的政治功能。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一文中明确表示,清廷兴黄教的目的是为了安抚蒙古诸部。北京地区有史可查的清代兴建的佛寺有31所,其中部分黄教寺院多是蒙藏地区上层政教人士的招待所和办事处,其政治性质十分明显。清代皇室祝寿时也往往修建佛寺,集喇嘛诵经,而且规模宏大,目的也在于抚绥蒙古诸部。特别是五世达赖、六世班禅、九世班禅先后进京朝谒清帝,具有强烈的政治用意,对蒙藏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清代黄庙是“民族的纽带”。
在这种“庙系天下”的政治色彩中还有一个连带因素。清代中后期,由于乡土因缘、经济布施,以及城区大型寺院清幽的环境,北京地区的许多大的寺庙或者成为权臣贵戚的“家庙”,或者与达官显贵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或者成为边疆大吏借寓下榻之所,如潭柘寺、戒台寺与恭亲王、西峰寺与醇亲王、贤良寺与李鸿章、法华寺与袁世凯、报国寺与顾炎武的关系即是如此。
三、“庙会商业”——北京地区佛教寺院文化特征中的世俗经济倾向
随着寺院政治色彩的逐渐淡出,乃至于政治地位的沦替,为了维持寺院的生存,保证一定的经济来源,不同的寺院根据其规模、地位位置及需求,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多数大型佛寺利用宏阔的庙院举办庙会,收取地摊费;而多数中小型寺庙则主要依靠出租房舍,也有的作为停灵柩房(长椿寺、宝华寺等),在寺院原有解决人神问题的基础上,又涉及到人鬼领域。这些行为大多数都不带有宗教色彩,只是经济行为,由此逐渐演变为民俗性质的商业活动,反映出清代北京地区佛教发展的世俗化经济倾向。
所谓“庙会”即因庙为市,缘起甚早。北京地区的庙会据说出现在辽代,明代已很兴盛。民国以后逐渐衰落(参见赵兴华著《老北京庙会·庙会的起源》)。老北京的庙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祭日定期开放,以进香敬神为主。信徒入庙进香,虽然也带些娱乐、商业活动,但基本上是附属行为;一种是以商业活动为主,在庙宇中定期开市,交易百物,又称“庙市”,主要内涵是市,日期根据贸易需要而定,不与宗教节日挂钩。庙会期间虽也有信徒进庙烧香叩头,规模小得多,是一种连带附属行为。
仔细分析北京地区庙会的集散地,佛教寺院占据主体地位主要在清代。清代初年考虑到八旗拱卫北京内城的需要,将庙市和灯市移至外城,庙市移至报国寺,灯市移至琉璃厂等处。雍正初内城隆福寺和护国寺开店设市,乾隆初开庙设市增多,甚至有“旧京庙宇栉比,设市者居其半数”的说法(《旧都文物略·庙市》)。
据民国初年统计数据,北京城内及郊区共有庙会36处,其中土地庙、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花市集、海王村公园、东岳庙合称“七大庙会”,但最为热闹的是东城的隆福寺和西城护国寺,有“东庙和西庙”之说,月开数市。所谓“都门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逢三则宣武门外之都土地庙,逢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九、十则东城之大隆福寺,俱陈设甚多,人生日用所需以及金珠、宝石、布匹、绸缎、皮张、冠带、估衣、古董,精粗毕备。羁旅寄客携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矣。”(《帝京岁时纪胜·都城隍庙》)《水曹清暇录·庙市》中也记载到“庙市,西城则集于护国寺,七、八之期。东城则集于隆福寺,九、十之期”。一般的庙会一年开一次,如大钟寺、黄寺、雍和宫在正月,万寿寺在四月,卧佛寺在五月,善果寺在六月等。
应该说,庙会的兴起有宗教方面的原因,尤其是节期庙会或许是起始于宗教节日,但随着社会的变迁,烧香礼佛的意义逐步淡化,商业和娱乐的内容不断扩大。两种类型的庙会有合流的倾向,而且商业经济在庙会中所占的比例日重。
清代乃至民国,北京地区佛教寺院庙会集散地有一个迁移兴衰的演变过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陶庐杂录》记载:“京师庙市向惟慈仁寺、土地庙、药王庙数处。后直郡王建报恩寺,兴市不数年王禁铜,即止。康熙六十一年敕修故崇国寺成,赐名护国寺,每月逢七、八日亦如慈仁请市,南城游人终鲜至也。重建隆福寺,每月逢九、十日市集。今称之为东西庙,贸易甚盛。慈仁、土地、药王三市则无人至矣。”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的《北京庙会调查》中曾分析庙会地点迁移的原因,“盖西城昔为满族及旗人聚居之地,日用所需多取给于庙会,故清代护国寺庙会甚盛。今则满族及旗人经济情况日下,护国寺因之遂衰。而东城则外人侨居,商业日盛,隆福寺遂因之发达。”
这种迁移兴衰的因素不在宗教方面,而是经济需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北京地区佛教寺院文化特征中政治色彩逐渐蜕化,逐渐演化为世俗经济的交易场所和集散地,反映出佛教发展的世俗化,寺院庙会的纯商业性质占据了主体。
四、“园林景观”——北京地区佛教寺院文化特征中的养性修真的取向
寺院说到底是僧人修行之所,信徒顶礼之处。因此构建清幽的环境是所有寺院文化特征中的共性之一。在建筑手法、风格上则各地区与各民族、乃至各地区独特的文化内涵相交融,各有取舍。北京地区的佛教寺院的主体是属于汉文化建筑体系,寺院建筑的基本规则未脱汉地佛教寺院的轴心中贯,左右对称,伽蓝七堂建筑格局(包括汉式建筑风格的藏传佛教寺院,如雍和宫)。
这种取向与交融在汉式传统建筑法式这一前提下,在建筑上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建于城市以接近朝廷的寺院建筑,取法于皇家建筑,乃至士大夫的宅院,多采取坐北朝南,轴线对称,重点居中,两翼为辅,构成时空合一的整体,从对称中显出庄严,而居于中轴线的主体建筑也以不同的高低规格展开一种内在的旋律,突出中心——大雄宝殿,虚实相生,构成整个寺院建筑的等级秩序。另一种是建寺于山,取法于道教修道成仙,建观于名山,相对灵活地建造山林寺院,以高尚佛心,同时也与印度佛教建石窟于山崖、苦行心性的隐修之志相吻合。但无论哪一种,都受士大夫情趣的影响,染带上园林风趣。当然前者建筑园林花园是点缀次要的,后者则深得汉文化的山林之趣。这种建筑风格取向在北京地区佛教寺院中显现得尤为明显。
在第一种城内建筑类型中,佛教寺院的建筑重点在于构建闹市区中的清幽,如外城法源寺的庭院以花木丰美而饮誉京师,西直门外的万寿寺结合庭院绿化而构筑亭阁山池;也有单独建造寺院花园的,如月河梵苑“池亭幽雅,甲于都邑”,成为京师的名园(见《天府广记》卷37引《月河梵苑记》)。
在山林建筑类型中,佛寺建筑重点在寻求养性修真的环境,所取得的成就,非同凡响。中国有“天下名山僧尽占”之说,北京西山地区颇有泉林之雅,为传统的风景游览胜地,早在金朝就已在此建造寺院,开后世先河;明代对西北郊的风景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开发,在西山、香山、瓮山和西湖一带建造了大量的佛寺,星罗棋布,数不胜数。甚至有“西山岩麓,无处非寺,游人登览,类不过十之二三”,“西山三百寺,十日遍径行”的说法。清代由于满清统治者视野的转移,大力营建西北郊园林,寺院的园林风格更是相得益彰。
明中叶后,以阜城门、西直门为起点,向西向北形成了几条明显的赏景路线和一连串的寺庙园林,每条路线中都有大小不一、规模不等的20~40所佛教寺院供游览欣赏。
在这些寺院中,敕建的和由贵族、皇亲、宦官捐资修建的一般都有园林,其中香山寺、卧佛寺、西山八大处、潭柘寺、戒台寺等,更是以其独特的园林风光、清幽环境知名于世。
从某种意义上说,园林寺院为寺院文化点缀上了休闲色彩,寺院也逐渐演化为休闲养性的场所。
五、“包容合流”——北京地区佛教寺院文化特征中的宗教内核
北京佛教寺院多种风格并存,反映出“包容合流”的宗教色彩,更揭示了北京地区的“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
北京地区佛教寺院既有典型的汉传佛教寺院,也有恢宏的藏传佛教寺院。从其宗教流派而言,据《松漠纪闻》云:“(金中都)燕京兰若(寺庙)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宗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金代末世,律宗与禅宗易位,中都佛门几乎成为了禅宗的天地,但其他宗派也在北京地区占据一定地位。尤其是元、清两代,藏传体系独盛于时。清代中后期以后,净土宗盛行,许多禅宗寺院实际上已经成为禅净合一的寺院。据1928年统计:北平城区有宗派可查的佛寺408所,禅宗的五大宗派基本上都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临济宗,更是以249所占据首位;但其他宗派,诸如贤首宗61所、南山律宗45所、法相宗6所等七八种流派,不可谓不多。
在检索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的佛教寺院法物记录时,发现佛教寺院与道教庙观中兼供两教神像的现象,而且不是偶然孤例。在道教庙观中经常出现佛教诸神造像,如文昌梓潼庙(档号J181-15-2)既供有文昌神像、魁星神像等,也有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部分关帝庙、真武庙常常并供佛教诸神。在佛教寺院也同样出现了这种现象,如弘兴寺(档号J181-15-111)中,有儒释道三像,关圣帝君为主,南海观音、地藏王菩萨、灵官、财神、韦驮等泥像十八尊;正良院(档号J181-15-140)佛道并供,有龙王、雨王等,更有释迦与罗汉;明建兴隆寺(档号J181-15-697)庙内法物有菩萨、关帝、罗汉、真武、火神等泥胎神像;毗卢寺(档号J181-15-769)庙内法物有木像毗卢佛像,也有关圣、山神、土地、二郎、龙王、娘娘等神像。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民间信仰淡泊、功利的反映。民间百姓对宗教的态度是为我所用,只关心烧香的效果,对庙属何教不感兴趣。为吸纳信众,寺院供奉诸造像的取舍标准也就逐渐脱离了自身宗派的束缚,采取了哪位灵验供奉哪位的功利主义态度。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出现,还在于宗教内含的包容性。以禅宗为例,流传的历史最长,甚至在明清之交还一度十分活跃,但清末基本上处于一种终结的状态,逐渐与其他法门浸没合一。在这种宗教思想下,北京地区佛教寺院供奉道教偶像,道观中供奉佛教偶像,佛寺、道观中供奉儒家人物也不足为奇。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包容大度”的心态和胸怀,也是北京文化的品格。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分工的细化,不仅北京地区寺院中存在的政治色彩逐渐淡薄,而且商场取代庙会,宾馆取代庙寓、赁房,殡仪馆取代寺院停灵,留存给寺庙的宗教修行功能逐渐单一化,文化品位中的休闲色彩日渐浓厚。
(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01,作者:张连城)

上一篇:春节习俗与汉传佛教社会生活
下一篇:吟山堂砚边芻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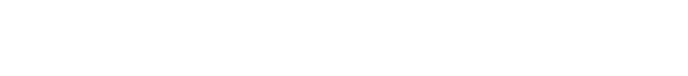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6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66号